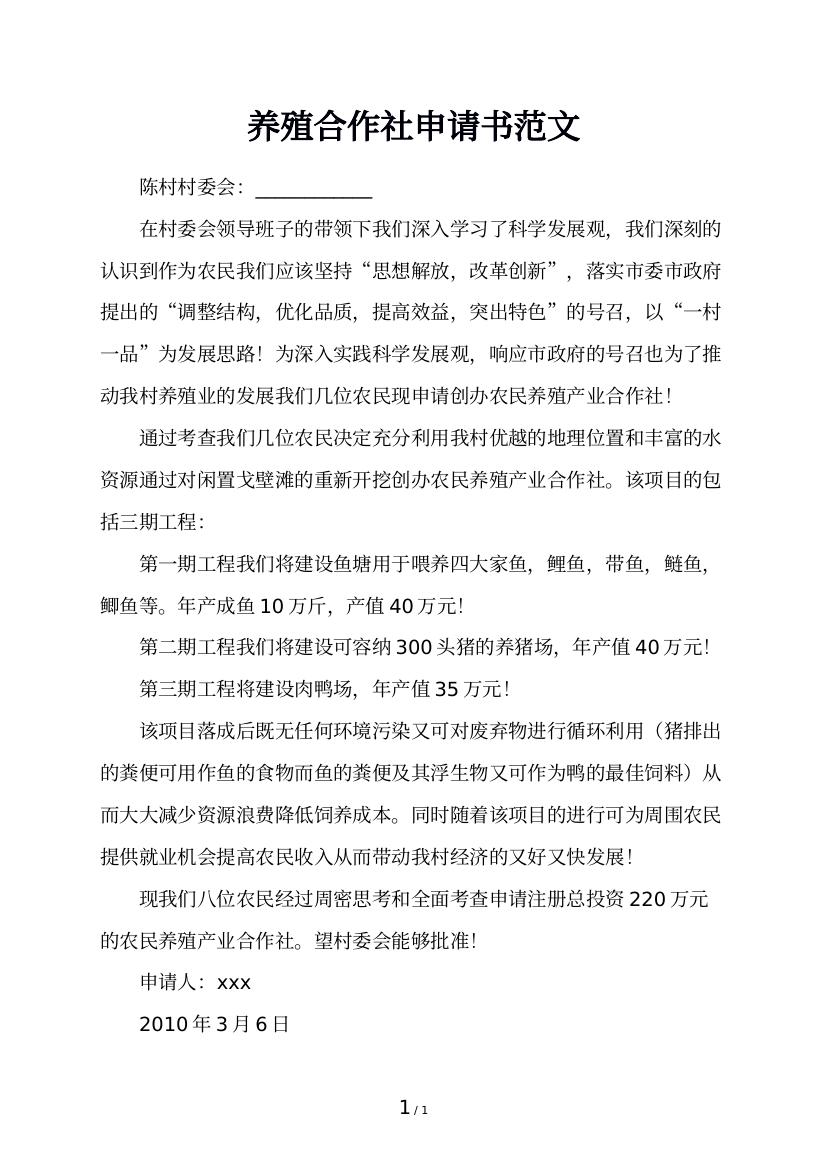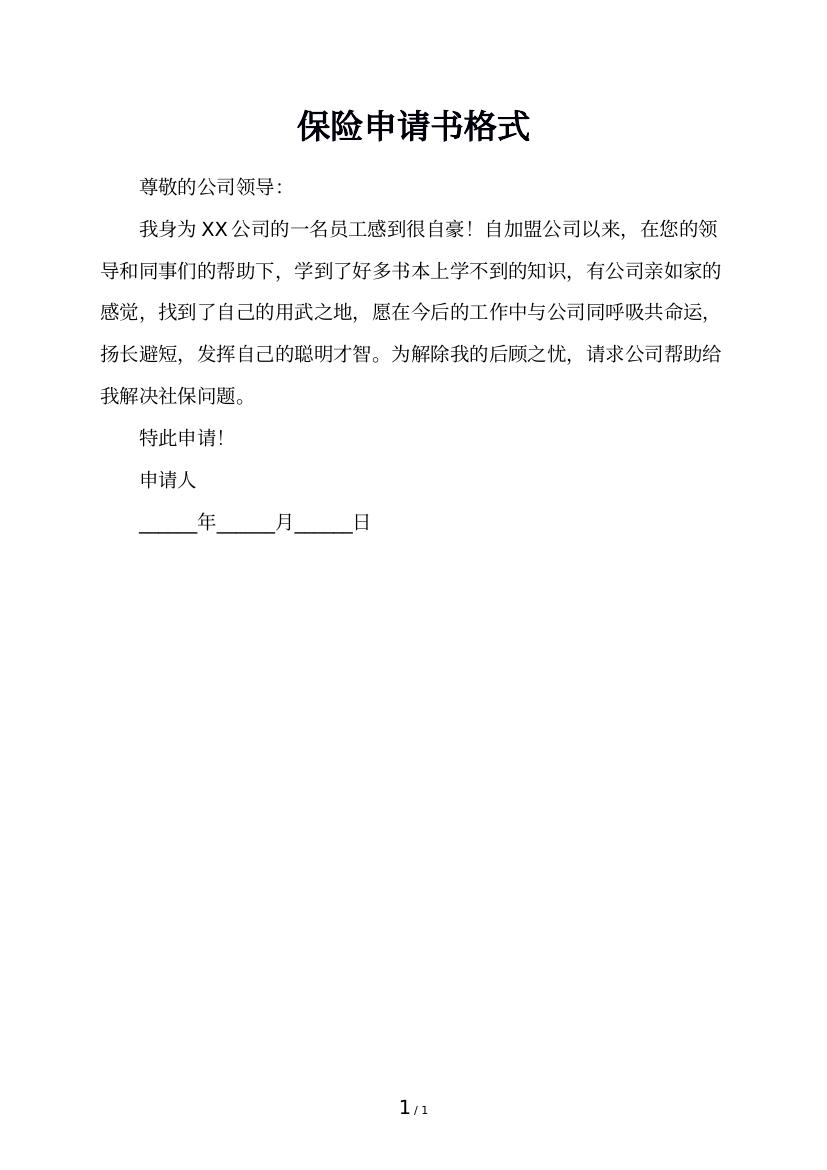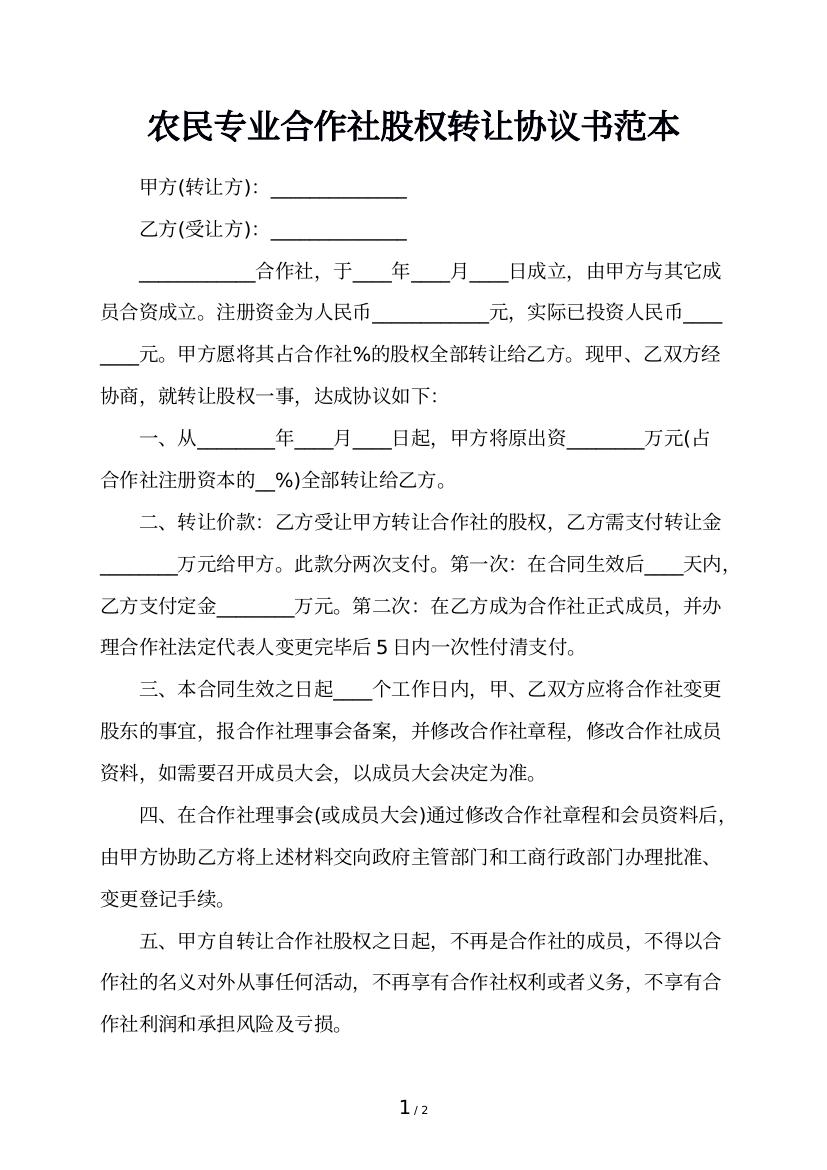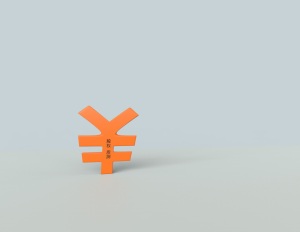善意取得仅仅适用于动产物权吗?
一、引言:问题及其分析主线
(一)问题的提出:善意取得仅仅适用于动产物权吗?
“善意取得”是一项比较奇妙的民法制度,即使我国民事法律至今尚未明确认可它的现实存在,但司法实务界对此并不感陌生,就我接触过的数百位民事审判法官和律师——他、她们大都有法科学生经历或者受过专门法律培训教育——而言,不知该名词及其大致含义者寥寥无几,这可能要归功于我国民法学理对其正当性的认可,从而给实务界人士提供了相应的智识营养。
在我国民法学理研究的语境中,善意取得的含义是:动产占有人对其占有的动产进行无权处分,作为取得人的善意第三人一般能确定地取得该动产物权。这大致包含了以下几个构成要素:标的物为动产、物权处分人为动产占有人、处分人没有相应的处分权、物权变动的基础是法律行为、第三人已经取得占有、第三人为善意。据此,善意取得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仅仅适用于动产物权交易,不动产物权交易不能适用善意取得。 [1] 这样,善意取得完全被动产物权“殖民化”了,善意取得内在地具有“动产化”属性,我们不能赋予其“姓氏”,因为“姓”动产物权是同语重复,“姓”不动产物权则完全错误,故而,善意取得和不动产物权是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任何关联的两套法律术语,我将这种理论称为“善意取得之动产化”。
何以如此,在我阅读范围内见到的理由大致有:其一,在不动产交易中,双方当事人必须依照规定变更所有权登记,不存在无处分权人处分不动产所有权的可能性,或者说不动产物权在交易中不致于使人误认占有人为所有人,这样,也就不存在适用善意取得的必要前提。 [2] 其二,不动产物权取得以登记为条件,这导致不动产权利具有明显的外部特征,不容易发生第三人不知情的所谓“善意”问题,从而,在绝大多数场合,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3] 其三,善意取得制度源于日尔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而该原则只适用于动产交易,后世的民事立法,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民法、英美法均效法该原则,只承认动产交易适用善意取得,不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4] 显见,前两个理由强调不动产物权的表征方式为不动产登记而非占有,而不动产登记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介入,排除了不动产物权交易领域内无权处分的发生以及第三人的“善意”,这抽空了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构建基础,使其成为空中楼阁;第三个理由则从比较法角度,得出善意取得仅仅适用于动产物权的结论,从而割断了善意取得与不动产物权的关联。[page]
由于持上述“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理论的论者均是学界中的重量级人士,这些论述的载体在学界又有崇高的地位——权威人物的学术著作以及权威的学术期刊,这意味着此种理论认识势将引起人们的共鸣,能在知识和分析进路上较容易地征服他人思想,由此,此种理论认识在我国民法学界已经成为强势话语权力。一旦这种理论认识成为制度现实,就会变成由国家权力支配的制度,其时,善意取得与不动产物权无关的界定就将走出学者的笔下或者口头,成为真实的客观存在。
这一切看上去顺理成章、合乎自然、毫无问题,但本文却意欲质疑这个理论,并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我的分析将否定“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理论,指出其在制度知识和认知方法上的缺陷,并得出善意取得不一定仅仅适用于动产物权的结论;而这样的分析显然针对的是这个问题:善意取得仅仅适用于动产物权吗?
我之所以要这样作,不是因为我喜欢“挑刺”和“抬杠”——有谁喜欢蛮不讲理、胡搅蛮缠之人?!也不因为我想借向名家“叫板”之机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一篇小文怎么可能达到如此效果?!而是因为在我看来,学术的生命不在于附随而在于反思和争辩,学术的进步不在于解释定论而在于在合理的基础上将既定结论不断“问题化”, [5] 更重要的还因为,换一种方法、眼光来探讨、凝视同一命题,无论得出的结果是证实还是证伪,都可能会把命题中蕴藏的力量或者问题更全面地展示出来,增添其再次问题化、再次论证的契机,从而促使其相对更合理、更有效、更实用,这才是本文的初衷。
(二)分析起点和基本思路
我的分析将从善意取得的概念开始。在大陆法系知识传统的熏陶下,法律概念是我们进行法学研究和学习的基本前提,不过,应当如何对待和理解法律概念,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可以将概念当作一种客观存在,其本身的正当性能通过思维体系的协调或者历史材料的证明表现出来,在这种意义上,概念是裁减社会现实的工具,符合概念之框定范围意义的现实才足以被纳入概念之外延。在我看来,“动产化”的善意取得概念,基本上属于这个思路的产品,因为它的智识资源主要来源于法国民法、日本民法这样的法国法系的法学素材,但由此产生的概念内涵却被普适于包括德国法系、英美法系在内的制度,在不同法系的制度和知识存在深刻分歧鸿沟的情况下,它的概念就要裁减那些功能属性相同的现实了,其结果就是善意取得被先在地冠以“动产化”的标记。比如,我们已经看到,“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理论的第一个理由就根据不动产物权的表征是登记而非占有,从而将不动产物权排除在使用范围之外,在此动产占有成了裁减被调整对象的工具标准。[page]
与这种认知方法不同,我们还可以采用功能分析的方法来认知概念,分析其中蕴涵的描述性成分和规范性功能成分,并将之适用于类似的或者相同的事实,这就把法律概念与具体事实结合起来,用法律概念来涵摄具体事实,再用具体事实来证实或者证伪概念,在此二者的双向互动过程中使它们得以最大程度的契合。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作为法律概念的善意取得,就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首先,善意取得描述了“无权处分”这个客观事实,这也是善意取得的适用前提,此处的“无权处分”是内涵私法自治意蕴的法律行为, [6] 是发生在物权变动之链条交易中的一个环节形态,这意味着善意取得要适用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场合;其次,面对无权处分的事实,善意取得的规范功能是保护第三人而非真实权利人,但为了给该功能赋予正当化的色彩,它要求第三人必须为“善意”,即不知交易前手是无处分权之人。显然,善意取得是对罗马法中“任何人只能向他人转让属于他自己的权利”这一经典格言的反动,它解决了在物权变动交易中如何从无权利人处取得权利这一现实问题,故而,它的含义能被还原为:通过附加善意条件而从无权利人处取得权利。
对善意取得的这种概念还原,表明本文的分析起点是先抹去善意取得的“动产化”色彩,以跳出“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理论的自足论证体系,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视野盲点。从这个基点出发,沿着功能主义的线索进展,我们将发现,不动产登记不能杜绝不动产物权领域中的无权处分现象,此种无权处分作为客观现实,为善意取得在不动产物权领域的适用提供了现实前提;而且,比较法考察的结果告诉我们,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则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同样要求第三人的“善意”。至此,“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的上述三个理由均被推翻,这种理论界定因此被“问题化”。进而,本文还将分析善意取得一体化——善意取得统一适用于整个物权领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并总结功能主义分析进路的意义。
二、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存在前提
(一)登记错误与无权处分
按照物权公示原则的基本要求,物权变动必须借助法定公示形式表示出来,由此产生的结果要有动产占有或不动产登记的外观表征,抽象的物权因这些外观而具体化,交易者也能通过它们而知悉权利主体、内容等信息。不动产登记作为权利外观之一,充当了表征真实不动产物权的信息平台,即“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物权”。如果将这个命题无条件地予以扩展,所推导出的理想结果和必然结论就是,在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之中的权利人和权利符合真实情况的前提下,登记权利人处分登记簿记载之物权的行为,当然是有权处分,那么,针对不动产物权的无权处分自然因登记介入交易而成为无稽之谈;既然不动产物权领域中不存在无权处分,善意取得也就无用武之地。一言以蔽之,只要坚持不动产登记决定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物权公示原则,善意取得与不动产物权就无关联。[page]
为了实现“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物权”的理论预设,人们设计了合理的不动产登记法来规范登记程序的操作和运行,以期达到尽善尽美的结果。然而,理想的追求往往被现实障碍所阻却。尽管登记要依照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但基于人之有限理性的致命弱点,由人设立和操作的登记程序的运行结果就像诉讼程序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德国给我们提供了实例,尽管德国土地登记法是后世仿效的楷模,但实践中仍出现本来不存在的物权被登记、本来存在的物权被消除等错误,其大致表现为:其一,合意与登记之间的背离,如V意欲将土地a转让给K, 却因双方过错将标的物确定为土地b,登记官将K登记为土地b的所有权人,这导致物权合意的标的不同于登记的标的,此登记即为错误; [7] 其二,形式合意原则,即登记官基于登记义务人的登记同意实施登记,而作为实体法要件的物权合意可能自始有瑕疵或者不存在,或者嗣后被废止,登记因此而自始或者嗣后无效; [8] 其三,登记官的错误,即因登记官的过错导致登记状态错误,如当事人双方订立了关于土地a的合同,但登记官却以土地b为标的进行登记;其四,在登记簿之外发生的权利变动,即依法发生的物权变动无需合意和登记,而其变动结果没有显示在登记簿上,如自盖房屋后没有进行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 [9] 在我国实践中,这些登记错误的现象及原因也并不陌生。 [10]
可见,理论假设在现实面前总是残缺不全的。登记错误的现实性,使得“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物权”成为理想图景,一旦其不能成为现实,登记所表征的权利与真实物权将兵分两路,登记权利人与真实权利人也要一分为二。在此情形,如果登记权利处于静止状态,第三人尚未介入权利人和真实权利人的关系之中,那么,此时不存在无权处分,法律要解决的问题是消除登记权利和真实权利的二元分离,恢复真实权利的登记外观以及真实权利人的物权人法律地位。一旦登记权利发生变动,登记权利人和第三人之间产生了移转房屋所有权、设定土地抵押权等法律关系,由于登记权利人实质上对不动产物权并不享有处分权,其处分登记权利的行为也就是无权处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因为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就认为登记物权人必定是有权处分人,这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采用尊重现实的态度,就应当承认登记错误的现实性,而解决登记错误造成的无权处分的思路之一,就是确立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 [11] 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物权利益,消除因登记错误而造成的混乱关系。
[page]登记错误造成的无权处分既为现实,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也就“恢复”了制度得以存续的根本前提,这当然也意味着支持“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的第一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二)不可忽视的程序保障
不过,问题并未因此而终结。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最终结果,是要否定原真实权利人的物权人法律地位,这无疑改变了事实的本来面目,而支持此种结局的最根本的正当理由,是登记形式和物权实质之间必须存在高度盖然性的相符关系,因登记错误引发的无权处分与建立在登记正确基础上的有权处分相比,必须属于极个别的例外,只有这样,扭正事实真相,才不会改变登记表征不动产物权的一般布局。
至此,我们已经看出登记错误与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之间的微妙关系:善意取得旨在解决由登记错误引发的无权处分问题,登记错误因此是善意取得实现的前提;但登记错误必须保持在人们可以容忍的低几率范围之内。如果登记簿的记载基本上不能正确反映真实权利关系,而法律允许在此基础上的善意取得,就势必在现实中频频出现“指鹿为马”的混乱,真实权利人的正当利益必将遭受不当损害。换言之,登记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但这种错误发生几率与登记正确率相比,在整体上要处于可忽略的程度,只有这样,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才能有正当性和生命力。由此看来,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仅仅是备用性质的规则,是为解决极个别情况而设定的,故其能否推行,还要看登记能否将可能出现的“指鹿为马”负效应降至最低,而这就只能靠切实可用的登记程序给予保障。
这一点在德国和瑞士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德国,登记程序中的审查对于登记效果真实的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主要类型——土地所有权移转以及地上权的设定、变更或者移转,采用实质审查方式,即登记机关除了审查登记申请是否符合土地登记法规定的程序要件外,在土地所有权出让的场合,还要审查当事人所为的物权合意、土地标示、物权合意的形式、 [12] 物权合意是否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13] 负担行为; [14] 在地上权设定的场合,登记审查范围包括物权合意、地上权条例规定的地上权内容、当事人约定的地上权内容。 [15] 其二,其他类型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只要符合相关程序规定即可,登记机关不审查物权合意等实体内容,属于形式审查。但是,由于登记是国家权力运作的表征,目的在于确定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和状态,故登记行为必须规范,登记结果应当正确,这就要求登记机关在实施登记行为时,必须遵循国家法律规定,达到登记程序正当,登记结果正确的后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登记机关可以突破形式审查的限制,比如,如果登记官知悉物权合意无效,就必须驳回申请, [16] 这时的审查范围就涉及了作为实体法律行为的物权行为;又比如,在不动产买卖合同因为欠缺必要的形式而无效时,登记机关就可以根据“取得禁止”制度,驳回登记申请, [17] 这时的审查范围超越物权行为之抽象原则的限制,涉及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基础行为的负担行为。[page]
在瑞士,登记机关审查的对象范围包括登记申请、不动产所有权人的书面声明、申请人的处分权利书证、法律原因的书证,其中的“法律原因”即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基础法律关系。由此,瑞士的登记审查不仅涉及登记申请等程序行为,还涉及到法律原因这样的实体法律事实,故属于实质审查。而且,在多数的依法律行为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情形,其原因行为须进行公证,否则即不生法律效力。 [18] 其原因在于,瑞士民法不把物权行为当作原因行为,故原因行为出现瑕疵,登记就会与真实不符,为了进行登记,需要就原因行为办理公证证书,以此来保持其确实性。 [19] 这样,在实体性法律行为以及其他法律事实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以及提出的文件不能证明法律原因存在的,登记申请即被驳回。
我们知道,德国、瑞士民法在依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上采用了强行登记的基本规则,不登记者不动产物权变动不能生效,登记在此具有代表不动产物权的含义,但这并非绝对真理,因为即使有登记,它也会发生错误,当然会存在无处分权人处分不动产物权的可能,当然也会存在第三人是否知道作为交易对象的登记物权是否真实的“善意”。 [20] 对于这些客观存在的现实,这些立法采用了现实主义的立场,它们肯定了不动产物权领域中无权处分存在的实际意义,并采用善意取得的立场予以应对,这是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得以存在的根本政策导向。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前文所指出的善意取得的描述对象和规范功能。但这尚不足够,它们又通过正当而严格的登记审查程序,为登记结果高度的正确性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使得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产生的剥夺原真实权利人物权的负效应降至最低点,从而确保了该制度在实践结果上的正当性。
三、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制度表达
仅仅证明不动产物权之无权处分的现实性,不足以表明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作为法律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因为这仅仅给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提供了可能,一旦立法政策不保护善意第三人,则其仍然是好梦一场。为了使美梦成真,我们还必须找出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制度实证。实际上,我们随手就能从德国法中找出这样的实例,而且,德国法的例子并非“一股独大”,其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从不缺乏盟友。这些实证法的出现,将建立在无权处分基础上的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一)德国法
德国物权法的发展历程具有浓厚的形式主义色彩,动产占有和不动产登记作为物权的形式外观,在德国民法中被赋予推定力(Vermutungswirkung )和善意取得效力(Gutglaubenswirkung),前者以法律推定的手段将公示形式表现出的权利作为真实权利,权利人对此无需主动负担举证责任;后者则以法律拟制的方式,在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公示形式反映的错误权利信息视为正确,确保第三人因信赖公示形式而取得的物权不被追回。这两种效力相互结合,共同打造了善意取得的制度框架。其中,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主要体现在德国民法第892条之中, 其具体规定为:“为权利取得人的利益,关于以法律行为取得土地的物权或者土地物权之上的物权的情形,土地登记簿记载的内容应为正确,但是如土地登记簿上记载有对抗此权利的正确性的异议抗辩时,或者取得人明知此项不正确时除外。为特定人的利益,权利人在土地登记簿上的权利受到处分权限制的,只有在该限制被记载在土地登记簿或者被权利取得人知悉时,才对权利取得人发生法律效力。”尽管该条采用了“ffentlicher Glaube des Grundbuchs(登记簿的公信)”,而不像规定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第932条直接采用“Gutglubiger Erwerb vom Nichtberechtigten(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但透过这些词语的迷雾,在法律制度体系化的视角里,它们从来就无根本差别,同属于善意取得的范畴,这一点为德国立法者所明确承认。 [21] 正因为这样,在德国民法文本中用立法语言表述的“登记簿的公信”,往往在学理中被表述为“土地权利善意取得”或者“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 [22][page]
在德国,除了受制于不动产和动产的物理特性而出现的公示形式区别之外, [23] 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和动产物权善意取得无甚差别,它们的相同点主要有:其一,制度价值等同,即以公示形式为载体来调整现实中的无权处分现象,达到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实现此价值的基本元素,是来源于日尔曼法的公示制度和罗马法的诚实信赖原则。 [24] 其二,制度基础等同,均为以权利外观为基础的信赖原则,即基于第三人对于动产占有或不动产登记的信赖,来确认其是否“善意”,并进一步确保其能从该信赖中实现预期的交易目的,最终产生善意第三人从无权利人处取得权利的后果。其三,制度构造等同,均包含三个主要构成要素:(1)物权变动交易链条具备连续的公示形式, 即无权处分人是公示形式所表征的权利人,第三人通过法定公示形式取得了物权;(2)第三人必须为善意,对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来讲,第三人不明知登记错误即为善意; [25] (3)善意取得行为属于交易行为,非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非交易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其四,制度性质等同,在物权行为理论的背景映衬下,善意取得之行为是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物权的行为,其中的善意因素弥补了处分人没有权利的瑕疵,使得善意取得成为正常有权处分之物权行为的异化表现,这保持了善意取得所涉及的交易行为的连续性,使其具备继受取得的法律属性。 [26]
德国法的这种制度构制,突破了其前世之罗马法、法国民法以及奥地利民法在善意取得上的动产化制度构造, [27] 在其特有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制度设置平台制约下,成为合理的“地方性知识”,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因此得以横空出世,这当然也就打破了“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理论从德国法中寻觅到的支持理由。
(二)瑞士法
瑞士民法除了承认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之外(第933条), 还认可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即该法第973 条规定:“出于善意而信任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内容因而取得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均受保护。”其制度价值、基础完全等同于德国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仅仅在制度设置上有所区别:其一,登记错误的判断标准不同。登记错误为不动产物权之无权处分提供了可能,因此登记错误的判断标准不同也直接导致无权处分的形态不同。瑞士民法没有采用物权行为之抽象原则的做法, [28] 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债权行为的效力直接关联着物权变动的效力,只要债权行为存在效力瑕疵,物权变动即不能完成,债权行为无效意味着据此而成立的登记是错误的;德国法则否认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在效力上的关联,债权行为是否无效与登记错误无关。其二,排除善意的判断标准不同。瑞士民法对于善意的排除具有灵活性,其标准为“凭具体情势所要求的注意判断不构成善意的,当事人无权援引善意”(第3条第2项);德国民法排除善意的标准很严格,仅仅局限于“积极知悉”或“明知”(positive Kenntnis)登记错误。[page]
(三)台湾法
同瑞士民法一样,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同样属于德国法系的成员。与瑞士民法相比,台湾地区民法虽然没有相应的明文规定,但实务普遍承认土地登记产生善意取得的绝对效力,而且台湾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简直就是德国民法的翻版,其除了维持原有的动产物权善意取得条文之外,又明确增加了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即第759条之一第2项规定:“因信赖不动产登记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为为物权变动之登记者,其变动之效力,不因原登记有无效或撤销之原因而受影响。” [29]
(四)英国法和美国法
再次,英国法和美国法也存在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迹象。虽然英国法原则上否认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但也有例外,即在土地必须登记的情形,无论买受人所指向的权利是否依据衡平法而移转给他人,只要该权利已记载于登记簿之中,就会产生善意取得的后果。 [30] 美国法则依据记录系统(recording systems)和其他规则,也肯定了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 [31]
上述立法例的出现,突破了善意取得因为“动产化”而没有“姓氏”的认识,表明善意取得不仅能“姓”动产物权,还可以“姓”不动产物权,表明仅仅对动产物权善意取得进行比较法考察,而忽视对不动产物权之规则的分析,是不能直接得出善意取得天然“动产化”结论的;显然,支持“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的第三个理由也不能成立。
四、善意取得制度的一体化及其限度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一体化
当物权公示原则在物权法中成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而不动产登记又有严格法律调控时,善意取得制度应当得到一体化的整合,它不仅能适用于动产物权,也应能适用于不动产物权,这将比“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的立场来得更为有力和有理。
首先,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与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制度安排目标一样,均是为物权变动交易提供法律保障,确保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取得。而且,它们均采用推定和拟制的法律技术,将“真”视为“假”、将“假”视为“真”,即在存在交易第三人、而且第三人信赖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占有形式的情况下,法律根据权利推定,拟制这些形式所表征的物权具有真实性,这样,就产生了“非真实”物权人被拟制为“真实”物权人,“真实”物权人被拟制为“非真实”物权人的结果。不仅如此,它们对第三人施加了严格的构成要件限制,比如要通过交易行为取得物权、必须善意等,这些构成要件虽然是为实现保护第三人的目标而设置,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协调第三人与真实权利人之间利益的作用。可以说,其二者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机制,应该得到一致的法律承认。[page]
其次,物权变动交易的法律效力应当具有等同性,不能因交易对象的不同而产生区别。物权变动交易依据标的物的形态可分为不动产物权交易和动产物权交易,前者以登记为公示形式,后者以交付为公示形式,这种相异的原因乃是交易对象的物理形态和利用性能存在的不同,这种区别在客观上要求法律采用不同的权利表现形式。但是,这些权利形式的法律效力不能受制于交易对象之间的区别,否则,就会产生同等性质交易产生不同后果的局面,不能同等保护交易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比如,据“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的理论,同一人基于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信赖,分别购买了房屋和机器设备,而登记权利人和占有人均为无权处分人,则买受人基于善意取得制度能取得机器设备的所有权,却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这种同等性质的信赖利益产生不同法律后果的情形,显然缺乏足够依据和理由。
再次,虽然学者常说,动产取得人应信任占有,有如不动产取得人应信任土地登记簿之登记, [32] 但与占有相比,经受严格法律程序形塑的不动产登记更值得信赖。占有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形式,其表征动产物权的作用是有限和不稳定的,比如,当同一动产出现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并存的多层次占有形态时,作为真实物权人的间接占有人要通过法律关系来实现对动产的支配,而没有占有动产的外观,这就导致直接占有不能反映真实物权,而这种不一致情况在现实中很常见。不动产登记则不因权利人是否对不动产进行物理支配而受影响,占有不动产者如果不是登记簿中记载的权利人,就不能被认定为物权人,而这种记载的法律事实是国家专门机关通过严格法定程序运行的结果,既有国家信誉的支持,又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交易者可以毋庸置疑地对其产生信任感,相信登记权利就是真实权利。可见,登记对不动产物权的表征是普适和稳定的,不受不动产占有情况变化的影响,与占有相比,登记可以更准确地反映物权归属情况和变动状况,当然也更值得信赖。既然在信赖占有的基础上可以设定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那么,在信赖不动产登记的基础上设定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的理由应更充分。
(二)善意取得一体化的限度
不过,我对善意取得制度之一体化的提倡,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而是采用“同情理解”的态度来关注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相应制度的替代。具体而言,一体化的善意取得是有限度的,至少在以下两种情形,认可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否定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也不无道理:
第一,不动产物权变动不要求强行性的不动产登记,而其他功能相当的制度能够妥当处理不动产物权变动交易中的第三人保护问题,自然也就无需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美国的产权保险(title insurance),即在不动产登记不健全的地域,美国产权保险公司几乎毫无缺漏地占有了所有证件资料,执行着与德国土地登记簿的功能相类似的任务,这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 [33] 除此之外,对抗性占有(adverse possession )制度也具有相当的功能。 [34] 在这里,不动产权利没有登记的表征,无从从登记错误中产生无权处分的现象,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自无其得以存在的现实前提。[page]
第二,虽然有不动产登记制度,但登记不能高度反映真实物权状况,登记不能承载让社会公众普遍信任的价值,在此前提下,即使第三人将错误登记信以为真,也不能取得不动产物权,这与动产占有的公信力功能恰好截然相反。这实际上是对法国民法和日本民法的客观写照,也是“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理论的来源。比如,日本之所以否定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登记簿本身相当不完全,而且构成不实登记的可能性也非常多(对建筑物尤甚)。 [35]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法国民法和日本民法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上,并不要求强行登记,而登记程序的构建也不足以保证登记的结果能一般地表征真实的权利,这样就会致使登记错误泛滥,一旦法律不加限制地促使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将会过分损及真实权利人的利益。 [36]
综上所述,从制度发展路径来看,是否采用善意取得制度一体化的策略,完全受制于不同法域的地方性限制条件,只要它们的选择能妥当处理无权处分不动产物权时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问题,妥当平衡善意第三人和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就分别有其合理性。对此,我们绝对不能采用“一刀切”式的“要么这样否则就必须那样”的做法,而应承认“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用德国做法来批判美国产权保险,如同用美国做法来评判德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一样,都有用自己的标准来评价他人行为之优劣的毛病,一旦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张“普洛克路斯武斯之床”。必须重申的是,本文的这种立场绝不是在“和稀泥”,而是表明善意取得制度虽然有一体化的可能和必要,但这种一体化并不绝对,它有它的适用限度。
五、结语:从规范主义到功能主义
(一)对规范主义的背离
在我看来,“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的理论认识包含的是规范主义的分析进路,它注重法条规范的逻辑自洽,而较少地从规范功能的视野来分析问题。首先,它通过不动产登记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介入,来推论不动产物权领域中无权处分的不现实或者第三人善意的不可能性,而这仅仅是思维中的推论,它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登记错误的实际情况却无情地击碎了这个思维结论,现实的确也存在不少的对不动产物权的无权处分。显然,光靠逻辑自洽的思维推论并不能达到“事物真的如此”的结果,要让人信服,还得给出经验实证材料才行。其次,在比较法运用上,其注重法律概念的比较,而没有更深层次地考虑该概念在各自法律制度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的确,法国、日本的不动产登记不具有公信力,在此种框架限定中,善意取得“动产化”无疑是合理的结论。但为了得出善意取得“动产化”的结论,而将肯定登记公信力的德国法与法国法、日本法放在同一知识层面进行求同分析,就没有注意到德国法系和法国法系作为两种不同制度构架,其中蕴涵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法并不相同,仅仅局限在概念层面上进行比较,忽视有什么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是什么的功能比较,最终导致“一叶遮目,不见泰山”。[page]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种规范主义的进路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它是我们了解法律制度的阶梯,否则,至少我就不会知道善意取得的大致含义。然而,我们又不能对其过于顶礼膜拜,特别是不能沉迷于围绕善意取得而搭建的概念世界之中,忘记了它背后的实际生活,而这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概念实体,一个概念的意义不在于其定义、形式以及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而在于它在真实世界中引起的后果。 [37] 这种见解,实际上也体现在王伯琦先生对概念法学的评析。在他看来,对于司法官或者行政官而言,不患其拘泥逻辑,唯恐其没有概念。但对法律概念的理解不能持僵化的态度,因为概念是概括抽象的,其本身并不就是真实。 [38] 的确,虽然概念是人思维的结果,但不是凭空由人的思维塑造出来的,它镶嵌在社会情境的意义网络之中,生活给予其真实内涵和正当性基础,单独认知概念并据此对事物进行归类,并不能使我们确知其中的正当性所在,只有在特定语境的整体价值网络中,我们才能全面、准确得知作为构成部分的这个意义。
(二)功能主义的运用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善意取得的分析和反思,起点是对其进行解构,通过“描述”和“规范功能”来把握其确切含义。其中,“描述”的对象是无权处分,“规范功能”的意旨是保护无权处分时的善意第三人权利取得。这样的解构抛弃“善意取得之动产化”那种先入为主的定论,放大了我们观察社会现象的视野。即除了要看动产物权领域的情况外,还要看不动产物权中是否有类似的情形、是否有这样的需求。这样,我们把善意取得的概念和规则重新放置在现实世界当中,看这个世界将会赋予它怎样的意义,它又如何妥当地顺从这个世界。是啊,“当人们将概念视为真实的存在,鲁莽地运用它们而无视逻辑对结果的限制时,它们与其说是人们的工具,毋宁说是专横的主人。当它们可能产生压制和不公时,我们最好将其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假设,应当受到限制与重构。” [39]
对善意取得的这种分析,完全将之视为工具——“以一种简略的方式辨识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的工作性工具”, [40] 制度是否正当取决于其“规范”意旨是否足以全面而稳妥地调整客观存在的“描述”对象,也即取决于这个功能在实际中是否好用、是否足够有用。这种分析进路属于起源于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即把一切文化事实放入它们所处的布局,在相关因素整体中理解我们要探讨对象的意义,同时,一事物为另一事物的函数,前者变则后者随之而变。 [41] 据此,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文化均是用来满足人之各种需要的手段,对其研究必须采用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方法。这种进路对法律现象的分析,不仅要看既有规则的含义,在相应规则体系的整体框架内关注其构成部分的意义,还要在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中,把握其进入制度世界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功能主义具有反思性,它不以概念实体和制度逻辑为唯一标准,而是从整体出发,首先考虑分析对象在关联系统中的位置,看这个位置对于系统整体的意义,以及与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之间互动函数关系,从而在整体框架内给分析对象准确定位。[page]
这种进路表明“善意取得之动产化”不能“描述”不动产物权领域中的无权处分,更无从解决由此产生的善意第三人保护问题,这为无“姓氏”的善意取得提供了界定“姓氏”的可能。更进一步,由于所有法律概念都有“规范精灵”, [42] 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它们的规范功能,对它们进行比较法考察,不能仅仅比较构成概念的术语,更要用体系的眼光来进行功能主义比较:首先,要比较那些在法律上完成相同任务、具有相同功能的事物;其次,必须对自己的“原始问题”进行反思,清除本国体系的一切教条主义成见;再次,问题的每一种解决方法,从其功能方面考察都是一个统一体,没有同功能相关联而只是比较各个解决措施,是很少有实益的,甚至会导致错误。 [43] 这意味着在采用比较法方法时,观察者必须尽量全面地观察所比较的对象,将之放在特定地域的整体制度以及关联因素制约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评判,将之定位为具有特定功能的关联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正如卢曼所言:“功能是一个必须在整个社会系统的水平上来解决的问题。每一个子系统相应地具有一项功能,这种制度安排要求每个子系统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上代替它。” [44] 这种放大视野的理解排除了单纯的规范主义,它要求我们必须看看法律规范的周围和背后,切不可仅仅从只言片语的规则中得出武断结论。
这样,善意取得就不再是真实存在的概念实体,它是人们用以规范特定对象的工具,它是否好用,要看其规范功能是否妥当,是否足以应对同类的“描述”对象。由此,我们看到德国、瑞士、台湾地区、英国、美国等不仅存在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也存在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善意取得因此可能被一体化,进而可以被冠以动产物权或者不动产物权的“姓氏”;而且,尽管我认为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和动产物权善意取得有理由一体存在,但同时认为也不要“一棍子打死”,我们还应当尊重那些在特定限制条件下走出另外道路的做法,给它们以同情的理解。
善意取得这枝域外之花受到了中国民法学理论的关切,但如何呵护它,不至于在花开蒂落之际长出“南橘北枳”之果,首先不能不采用功能主义的方法来认识它,界定它的基本内涵,解析它的外围要素,框定它在相关制度系统中的位置;再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附以合适的土壤和养料,具体而言,如果我国的物权法将贯彻德国法系的物权公示原则,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上采用强行登记的策略,那么,登记错误以及无权处分的发生就可能要求用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予以规范,但此时不能忘记的就是必须有正当而合理的登记程序的保障,否则,正如前文所言,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将失去其正当性,善意取得也就仅仅适用于动产物权了。 注释:[page]
[1]如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页243—246;钱明星:《物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208;梁慧星、 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页185;魏振瀛主编:《民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240—241;杨立新:“共同共有不动产交易中的善意取得”,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4期;孙宪忠:“再谈物权行为理论”, 载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201; 中国政法大学物权立法课题组:“关于《民法草案•物权法编》制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另外,我国台湾学者谢在全先生也持相同的见解,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21—222。
[2]杨立新,同上注;中国政法大学物权立法课题组,同上注;梁慧星等, 同上注,页185;谢在全,同上注,页221—222。
[3]王利明:“再论善意取得制度”,载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4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207;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页238。但王利明教授同时又指出, 不动产交易会因登记错误、疏漏、未登记等原因发生无权处分问题,第三人同样存在是否知情的问题,即是否为善意的问题,如果不动产交易中第三人取得不动产时出于善意,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秩序的目的出发,应当允许第三人获得不动产的所有权,这样,不动产也应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4]杨立新,同前注1。
[5]福柯即指出,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147。
[6]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55—56。
[7]在物权行为体系要求下,德国民法第873条第1款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采用“合意+不动产登记”的模式,不动产登记的正确性,要依据登记是否与合意(即双方物权行为)相互契合来判断,契合者即为正确。
[8]出于交易便捷的考虑,德国土地登记法第19条允许用登记义务人的登记同意(这是程序行为)来替代物权合意(这是实体法律行为,即通常所谓的物权行为),这样,登记审查的对象就不涉及作为实体法律行为的物权合意,但会导致登记同意内容偏离物权合意,从而致使物权合意与登记内容不符,这就会出现登记错误。[page]
[9] Baur-stürner, Sachenrecht, 17. Aufl., Verlag C. H. Beck, 1999, S.190—192.
[10]常鹏翱编著:《物权法典型判例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页133以下。
[11]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此的用语是“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而非“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所以要作出这种区分,是因为这种善意取得的对象,局限在所有权、他物权、顺位等不动产负担的物权性利益范围之内,以不动产为标的物的债权、税收等国家公共负担不以登记为存续要件,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动产的形态、面积等事实状况以及当事人行为能力等个人事宜,虽然也记载于登记簿之上,但登记机关不可能随时跟踪它们的变化情况,无从保证它们的真实性,故它们也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因此,“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不宜称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否则就会从基本概念上不当扩大该制度的适用对象,造成不必要的认识混乱。
[12]德国民法第925条第1项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出让双方当事人应同时向登记机关、公证人或者法院表示有关出让所有权的物权合意(Auflassung)。
[13]德国民法第925条第2项的规定, 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的土地所有权出让无效。
[14]德国民法第311条b和第925条a的规定, 土地所有权转让的负担行为必须采用公证的形式。
[15] Holzer-Kramer, Grundbuchrecht, Verlag C. H. Beck, 1994, S.79—80.
[16] Schwab-prütting, Sachenrecht, 27. Aufl., Verlag C. H. Beck,1997,S.118.
[17] Wacke:“德国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合意与登记”,孙宪忠译,载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703—704。
[18]参见瑞士民法第499条、第512条第1项、第657条、第712条d、第746条第2项、第783条第3项、第779条a、第799条第2项。
[19]我妻荣:《日本物权法》,有泉亨修订、李宜芬校订,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页224。
[20]既然不动产物权领域会出现登记物权形式与真实权利的背离, 第三人也就会有对此是否知情的善意、恶意,这一点与动产物权善意取得是一致的,而下文有关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之制度表达中对第三人“善意”要件的规定,也印证了这一点;这当然也推翻了“善意取得之动产化”的第二个理由。
[21] Olzen, Zur Geschichte des gutglubigen Erwerbs, Juristische Ausbildung, 1990, Heft 10, S. 505.[page]
[22]在德国物权法文献中,明确采用善意取得解释民法第892条规定的,可参见Weirich, Grundstücksrecht: Systematik und Vertragsgestaltung, Verlag C. H. Beck, 1985.; Gerhardt, Immobiliarsachenrecht: Grundeigentum und Grundpfandrechte,2. Aufl., Verlag C. H. Beck, 1989.; Haegele-Schner-Stber, Grundbuchrecht, 10. Aufl., Verlag C. H. Beck, 1993.; Wieling, Schenrecht, 3. Aufl. Springer Verlag, 1997等。英语文献的解释,参见Nigel Foster, German Law & Leagl System, Blackston Press LTD., 1993,p.248.
[23]当然,从制度发展的路径来看,这两者也存在不同, 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制度之源可以追溯到日尔曼法中的“以守护手”规则,但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则主要产生于中世纪之后的德国诸邦的不动产法之中,对此,可参见Olzen, aao;Buchholz, Abstraktionsprizip und Immobiliarrecht, Klostermann,1978。但这种制度发展史上的差别,并不影响它们在制度实质上的等同。
[24]向明恩:“德国民法一百年之回顾与展望”,载《东吴法律学报》第13卷第1期。
[25]德国不动产善意中的“善意”标准是“不明知”, 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标准是“不明知或者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之所以产生这种区别,是因为作为公示形式的不动产登记与动产占有相比,前者由法律组织(登记机关和登记官)和法律制度(登记法)的保障,一般都能反映真实的不动产物权,这样对第三人善意的要求程度就相对要低,即不知登记错误即可;而动产占有对权利的推定会往往被占有改定等打破,会出现占有人和实际权利人的分离,为了保护实际权利人,法律就提高了第三人的善意标准。王泽鉴先生也指出,在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是指不知土地登记的不正确,有无过失,在所不问,这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相区分,能强化土地登记的公信力。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版,页124及该页注2。除了这个区别之外,德国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中的“善意”和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中的“善意”内涵并无根本差别,对此,可参见Wieling, aao, S. 111—114 und S. 272—274.
[26] Schwab-prütting, aao, S. 101 und S. 204.
[27]不过,奥地利民法在以后修改了其原初的规定, 认可了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对此,可参见Stadler, Gestaltungsfreiheit und Verkehrsschutz durch Abstraktion, J. G. B. Mohr, 1996,S. 512.[page]
[28]有关瑞士民法肯定物权行为之分离原则, 但否定物权行为之抽象原则的分析,可参见Stadler, aao, S. 512—514.;苏永钦:“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载苏永钦:《跨越自治与管制》,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页245。
[29]王泽鉴:同前注(25),页122—123。值得提及的是,王泽鉴先生在其著作中,明确区分了“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和“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参见王泽鉴,见前注(25),页121—126;王泽鉴:《民法物权》第2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47—313。
[30] Wolf, Sachenrecht, 15. Aufl., Verlag C. H. Beck, 1999.S.219.
[31] Stadler, aao, S. 515—517.; D. B. Burker,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Little, Brown und Company, 1993,p.163.
[32]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23。
[33]与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相比,产权保险可谓是“功夫在诗外”。 产权保险与美国查阅土地证书链条的交易习惯相配合,由高额成本、专业人员以及特殊保险行业提供金钱、智力和职业支持,无论在交易习惯、制度操作,还是在金钱、智力和职业的限制要素方面,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有关产权保险及其评析,参见Stadler, aaO, S. 531—532.
[34] Carol M. Rose, Possession as the Origin of Property, 52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Winter1985.
[35]我妻荣,见前注19,页43。不过,为了解决不动产物权领域中因无权处分产生的第三人保护问题,日本司法实务采用了类推适用民法第94条第2 款关于虚伪意思的策略,田山辉明:《物权法》增订本,陆庆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31。尽管这种制度在适用上比较繁琐,但也能保护第三人的利益。
[36]对此更进一步的分析,参见常鹏翱:《物权程序的建构与效应》, 特别是第三章“物权程序建构的正当性标准(一):工具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民商法学专业法学博士学位论文。
[37]波斯纳:《法律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页21。
[38]王伯琦:“论概念法学”,载王伯琦:《王伯琦法学论著集》, 三民书局1999年印行,页33—50。
[39]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页129。[page]
[40]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484。
[41]马凌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页65;A.R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潘蛟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03;绫部恒雄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页24以下。
[42] Kaufmann, Rechtsphilosophie, 2. Aufl., Verlag C. H. Beck, 1997, S. 97.
[43] 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56—58、77。
[44]卢曼:“法律的自我复制及其限制”,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韩旭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448。
出处:《中外法学》2006年第6期